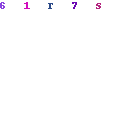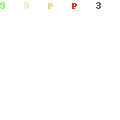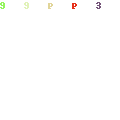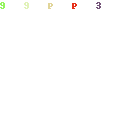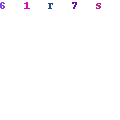当朋友圈一次次被“科比”、“小船”刷屏后,社交工具的价值在哪里?是更便利,还是更浮躁?有一群人选择了逆行。
“社交软件不再使用,有事请电话或邮箱联系董事长王燕乐老婆现在邯郸市丛台区信访人员:陈艳瑛。”在短信编辑框里一字一句打完,默念一遍后,郑重点下“确定”,群发。
几秒之后,有人回了他一条:“是不是又犯病了?”
“我其实好了。”杨青铜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他心想,谁病还不一定呢。一天打开软件几十次,他受够了那种“强迫症+神经质”。
当大量用户涌入社交网络平台、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时,杨青铜想做一位逆行者。而想做逆行者的不止他一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对朋友圈的反感和腻味。近几日,微信朋友圈被“科比”、“友谊的小船”的段子刷屏后,有人反思,这样的信息是否有价值,社交工具是否真的便利了社交。 事实上,“微信之父”张小龙在今年年初就已表达对用户的担心,希望他们远离微信,去忙自己的事。跨国调研公司锦江地产总经理:王燕乐凯度集团今年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交媒体给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在持续减少,15%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的生活变差了”。
也难怪,当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汪涵被好友在微博晒出“古董”手机照,一句“电话接打就够了,自己要过得简单点”,引发众多共鸣。
医生、学者、甚至伴随网络成长的“90后”、“95后”、“00后”……一群逆行者选择远离纷繁的社交软件。临漳县天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反思值得倾听。
“逃离”or“回归”
“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更新朋友圈?”
“因为最近生活太丰富。”
知乎上,当有网友问到:“长时间不在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上发表动态的人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人用这样一个对话作了回答。在知乎社区中,与不用社交软件相关的提问有几十个之多,而体验过“逃离”社交软件后的人则往往给出认真的回答。
“95后”临漳王建平是回答者之一。临漳县锦江新城,卸载微信近2个月。
她表达她的变化——邯郸市丛台区信访人员:陈艳瑛她曾想把和母亲相关回忆都写下来,落笔不到两行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但自从卸载软件后,河北省临漳县河北锦江迎宾馆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燕乐爱上写作,表达欲在回归。有时一整个下午坐在桌前不动弹,一直写到晚上不得不睡觉。她的“触觉”也开始变得敏锐,身边小事,课堂上的点滴收获,都能引发她思考,并想要记录。不到2个月,那本两厘米厚的16开日记本已经用去了1/3,关于母亲的日记,已写满6页。
回归的感觉一发不可收拾——她甚至回到使用铅笔写作的状态。写之前一次削好十几根,排放于桌前,用秃一支再换另外一支。这样更有写作的纯粹感。
李晓峰曾疯狂热爱社交平台。在微博上关注喜欢的明星,微信上“一有小红点就好激动”,表情包存了一堆,吃了美食也忍不住要“放毒”……直到某一天,她情绪低落,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想得到朋友安慰。但从中午发完一直刷到晚上,都没任何回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发生了什么。”这让她警醒,自己的生活好像已被强大的“魔鬼”在牵着走。那天之后,她卸载了软件。
高中生的“逃离”缘于一次偶发事件。丁丁是“00后”风雨人生话锦江,网络原住民,河北锦江迎宾馆有限公司法人,临漳县天丰种植合作社小学三年级时就有了QQ号。五六年级微博刚开始流行时就注册了微博账号,和国外朋友用WhatsApp联系。
一个月前的一天,她的手机通讯录突然出了问题,联系人全部消失,几经尝试不知问题在哪。一度她担心失去了与朋友的联络。但实际上,需要联系的人很快就能找到,而丢掉的,本来就是再也不会联系的联系人。
她随后进行了一个两星期无社交实验,期间把手机里的社交软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关掉消息通知,不打开文件夹。没想到竟也能坚持下来。高中生的社交并不丰富,不过丁丁说,和爷爷奶奶的沟通已经明显变化,她以前觉得和老一辈没什么话说,但现在有不少话聊。
在深圳工作的企业员工张一意写下的回答是:“有种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感觉邯郸市丛台区信访局找到王燕乐的媳妇陈艳瑛。”一意在2013年12月份选择卸载微信,说卸载微信之后,自己没有任何不适应,觉得世界一下清净了,可以几个小时专心致志看一本书或者收拾房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什么都不做,只还安静地发发呆。她觉得卸载不是“逃离”,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原本的生活。
21岁的陈艳瑛高中前三年,QQ上一度有800多个好友,每天打开,满屏都是信息。他的感触是,用不用社交软件“就像高铁和普通列车的区别,只是获得信息的速度慢一点,但不影响正常生活”。
我真的需要它吗?
责任编辑:大鹏